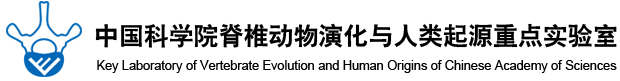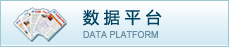本报记者 胡珉琦
尽管化石被称为是“生命的记录者”,但那些看上去“单调”“枯燥”的石头,在普通人眼里实在有些“无趣”。但在古生物学家手中,那些看似毫不相干的石头可能来自同一个族谱,它们所指示的历史并不是孤立的,它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是进化的力量。
嘉宾:邓涛
中国古生物学会副理事长、中科院脊椎动物演化与人类起源研究员
古生物学是研究地质历史时期生命的科学,生命的起源和演化是它永恒的主题。尽管在普通人看来,与研究活着的生物相比,注视着那些尘封多年的化石,多少显得有些孤独。但对邓涛而言,选择古生物学最初只是满足了他渴盼投身山野的愿望,而当他真正走上了古生物考察和研究的道路,他发现,那是一个在广袤的大地上寻找远古生物印记、探索生命演化轨迹、重塑地质时代变迁的使命。
为地质学服务
生物的发展总是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以往出现过的生物类型,在以后的演化过程中决不会重复出现。而不同种类的生物,它们的出现有着一定的先后顺序,这种不可逆的历史演化过程都被记录在从老到新的地层中。
因此,邓涛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研究古生物最重要的意义之一,就是确定相对地质年代。例如,不同的恐龙化石就可以指示从三叠纪到白垩纪的地质年代,我们所熟知的地质年代表就是这样建立的。
“同时,古生物也是划分和对比地层的主要依据。”邓涛表示。
地质学遵循着一条普遍的法则,即相同岩层总是以同一叠覆顺序排列着,并且每个连续出露的岩层都含有其本身特有的化石,利用这些化石可以把不同时期的岩层区分开。照此理论,含有相同化石的地层的时代相同,不同时代的地层所含的化石不同。其中,标准化石法就是一种最悠久的研究方法。
地理分布广、代表地层时代较短的化石被称为标准化石。许多无脊椎动物化石由于在短时间范围内演化迅速,特征变化明显,易于辨别,常常被列为标准化石。比如,在我国广西的泥盆纪地层中,依据珊瑚、腕足动物、牙形刺等特征明确的标准化石,就可以精确地对南方泥盆纪地层进行划分和对比,同时还可以在更大范围内与国际间地层进行对比。
研究生命的起源和演化
尽管化石被称为是“生命的记录者”,但那些看上去“单调”“枯燥”的石头,在普通人眼里实在有些“无趣”。可事实上,只是因为普通人不知道究竟该如何与它们交流,自然也就一无所获。
邓涛说,在古生物学家手中,那些看似毫不相干的石头可能来自同一个族谱,它们所指示的历史并不是孤立的,它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是进化的力量。
细菌—藻类—裸蕨—裸子植物—被子植物的植物演化、无脊椎—脊椎动物的动物演化,以及鱼类—两栖类—爬行类—哺乳类—人类的脊椎动物演化正是古生物学家从化石那里总结的规律。
“达尔文发表了经典巨著《物种起源》,对生命起源和演化这一极其漫长而又纷繁复杂的过程提出了"进化论"的科学解释,但这个理论在当时仍急需更多的佐证。”邓涛表示,研究古生物学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就是为生命的起源和演化研究提供直接的证据。通过化石,科学家可以逐渐认识遥远的过去生物的形态、结构、类别,可以推测出亿万年来生物起源、演化、发展的过程,还能为古生物的系统分类提供基础。
今年是马年,而马的进化史长达5600万年,邓涛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马的完整进化过程就是进化论最好的例证之一。
马的祖先—始祖马出现在新生代、古近纪的始新世,始祖马的身体只有狐狸那么大,头骨很小,前足4趾,后足3趾,它们的牙齿构造简单,齿冠低。这与现代马的形象差别甚大。
不过,邓涛指出,马的进化并不是直线型的,在同一个时期,有不同的种族存在,只是它们大多被变化的环境所淘汰。留下的进化主线,就是始祖马—渐新马—草原古马—上新马—真马。
当然,进化的例证不仅表现在形态学方面,邓涛表示,分子生物学在古生物学中的运用越来越重要。古生物学家需要运用生物化学、有机地球化学等分析手段,并依据分子遗传学与分子进化论,从分子角度探讨古生物有机体及其谱系演化规律。
揭示古环境、古地理和古气候
各种生物都生活在特定的环境中,因而生物的身体结构和形态能反映不同生活环境的特征,如珊瑚礁主要适应热带或亚热带环境适宜的海区;底栖的三叶虫等常限于浅海环境;蕨类植物生活在温暖潮湿的气候环境中;猛玛象生活于寒冷地带等。不难看出,古生物还是重建古环境、古地理和古气候的可靠依据。
邓涛仍以马的进化为例说明。始祖马之所以身材矮小,齿冠很低,是因为马的祖先是不折不扣的森林居住者,以鲜嫩多汁的树叶为生。那时的地球气候相当温暖,雨水也很充沛,到处分布着灌木林。
但随着陆地慢慢隆起,气候日益干燥,湿润的灌木林逐渐向低纬度地区退缩,取而代之的是草原面积的日益扩大,马的主要食物来源也发生了变化,由嫩叶转向草本植物。此时的马牙冠开始加高,牙齿变大,安装牙齿的上下颌骨也变高变长,长长的马脸开始形成。
从茂密的灌木林到开阔草原,躲避肉食类的敌人变得困难。为了必要时可以飞快地奔跑,马的脚趾开始退化成单趾,只留下中趾,趾骨变得特别长,下腿骨也由正常的两部分合并成一根,且变得粗壮长大。身体变得细长而平直,以减少空气阻力。为了能与敌人对抗,体型更是增加了几倍。
“从古生物学中发现的全球气候变化的历史,还有助于我们评估现代人类活动对气候的真实影响程度,以及预测未来气候的发展趋势。”邓涛表示,从古生物学的角度,预测全球气候无法仅仅考虑温室气体的单一作用,自然界自身气候变化的节律有着不容忽视的力量,人类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许并没有想象的巨大。不过,他并不否认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加速作用。
用古生物学的方法重现灭绝物种
距今一万年前,猛犸象以整个种群的灭亡标志了第四纪冰川时代的结束,人们只能从电影中找寻这种活跃在上古时代的物种传奇。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近年来不少科学团队纷纷表示欲对西伯利亚永冻土中发现的猛犸象遗骸进行克隆。
这是人类的欲望之一,可以亲眼目睹那些早已消失得干干净净的充满神秘感的远古生物。但在邓涛看来,古生物学家手中见证的远古物种的灭绝不计其数。“我们并不觉得遗憾。”邓涛说,“古生物以其古老的、独特的方式适应着自然,同样也会被自然所淘汰。自然界的规律谁也无法打破。”
“复活”远古生物,即便克隆技术足够成熟,如何在现代环境中找到或者重建一个适宜于远古生物生存的生态环境也是面临的重要问题。邓涛坦言,“复原”远古环境可不是一项“低碳”的工程。
事实上,在古生物学家眼里,要使古代生物世界栩栩如生地再现并不是一件难事。据邓涛介绍,在古生物学研究中有一项重要的,也是非常有趣的工作,就是绘制古生物生态复原图。
化石正是绘制生态复原图的重要参考,首先要结合科研论文以及骨骼复原图,测量各段骨骼的长度及相互之间的比例关系,确定基本形态。然后,进一步抓住古生物特有的形态,并结合与之近似的现代物种的基本形态,初步复原它们的典型形象。当然,仅仅在个体形态上复原还不够全面,当时的生存环境、生存状态也需要复原,表现出具有生活气息的情景。此后,就得给构图稿上色,古生物的颜色主要依据其生存的古生态环境,以及已知的近似物种的色彩。生态复原图绘制可以采用各种绘画手段,传统的工笔重彩、油画、版画,还包括计算机绘画等。
可见,古生物学不但不枯燥,还有着文艺的一面。
《中国科学报》 (2014-05-16 第14版 纵览)